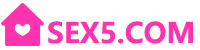男同 影片 李辉|香港九华径,流一火者曾经的“鱼米之乡”
发布日期:2024-12-09 21:55 点击次数:171
 男同 影片
男同 影片
文 | 李辉
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间,香港一个不有名的小村九华径,曾住着好多因遁入内战逃一火香港的内地文士。六十多年昔时了,这个小村依然如旧。
一、端木蕻良狗爬径写牧歌
四姐四姐件件行
大事小事两手清
区公所里管地亩
皎白好像琉璃灯
……
剩下七妹是个幺
纺出棉线一长条
纺给姆妈织棉布
棉布织成过红桥
大开一九四九年春天的香港《大公报》副刊,可读到一个吞并性的诗配图专栏,名曰“狗爬径牧歌”。牧歌由端木蕻良所写,木刻配图由黄永玉所做,每隔几日,一图一歌。上头所引,恰是“狗爬径牧歌”的《七姊妹》中的两首。
狗爬径——一个奇怪的、土得掉渣的地名。黄永玉先生说,这是他和端木蕻良等一批内地人,当年在香港远郊居住过的一个小村庄。村里小路,沿山坡而上,褊狭迤逦,七高八低,人行走之上,如同狗爬山,这一村庄故被人称作“狗爬径”。自后,狗爬径有了一个新称号:九华径。
以“九华”替代“狗爬”,应是两者发音相近之故。新称号天然很好意思,不外,却少了旧称的形象与景仰景仰。难怪开设新的牧歌专栏时,端木蕻良和黄永玉,仍以“狗爬径”定名,大要议论到它与“牧歌”文体更为吻合。
谁能猜度,即是这么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平凡小村庄,在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技能,因遁入内战逃一火香港的诸多内地文士,积聚在此。也在此居住过的漫画家方成曾回忆说,他是应黄永玉所邀住进九华径。
除黄永玉、端木蕻良、方成以外,先后在九华径居住过的作者、文士、画家等文化人士有:楼适夷、黄薇佳耦,臧克家、郑曼佳耦,蒋天佐、陈敬容佳耦,巴波、李琪树佳耦,考诚、殷平佳耦,李岳南、叶筠佳耦,阳太阳全家,王任叔(巴人),卞之琳,杨晦,耿庸,余心清,单复,朱鸣冈,顾铁符。画家陆志庠住进黄永玉家,作者张天翼住在楼适夷家。此外,还有《金陵春梦》的作者唐人。因他们居住在此,频繁有其别人打听。黄永玉铭刻,胡风来到楼适夷家,一夜恳谈。萧乾、聂绀弩、乔冠华等人曾经前来。方成铭刻,周而复、秦牧、李凌、谢功成、刘式昕、叶素以及“红尘画会”的画家们,都来作客……
小小九华径,一时群贤毕至,蔚为壮不雅。
二、小村依旧
知谈九华径的名字有些年头了,也熟练不少曾在此居住过的前辈,我却一直莫得前去寻访的念头。方成早在一九八三年就惊羡过:“离开香港三十多年了,阿谁小村庄只怕早已被高堂大厦吞没,少量也剩不下。”又是三十年昔时,在寸土寸金的茂盛香港,我猜想九华径只怕早已消散了,即便前去,当年脚迹已不大可能看到。
前些年一次去香港,安逸了王新源兄——一位村生泊长的香港人,虽是诡计机各人,却亦然一位香港文化通。王兄与我一样,对老一辈文士的故事津津隽永。巧的是,一年前他刚刚寻访过九华径,告诉我,九华径如故一个老屯子,简直如故友花样。一听,无妄之福,我当即毁灭其他筹谋,与之相约,次日一同赶赴九华径。
九华径位于九龙荔枝角,乘地铁知交意思孚站下车前行,走路约一刻钟,拐进一条马路,路的左侧,一棵大榕树洒下一派约几十平淡米面积的浓荫。树前,竖一块铭牌,绿框白底黑字,以中英晓谕写五个大字——“九华径旧村”。咫尺即是狗爬径——九华径。
委果没猜度,香港竟还存有这么一个老屯子。青山环绕,绿荫重重,一条小路,不到两米宽,由水泥、石板交杂而成,从大榕树运行沿小溪向山坡之上蔓延,这即是统共这个词村庄的主动脉。小路两旁,高下不一的老配置与由绿色铁皮搭建的棚屋,组成旧村的破落生僻,偶尔一幢两幢齐备的老配置,显出旧日的风格,但墙壁上则已布满斑驳碎影。不少老屋子空置,或者,索性惟有残垣破壁。一家当年药店,屋子已无脚迹,空旷的深谷上,只剩下一根砖砌柱子,婉曲可见红土所书“保康宁药行”五个大字,孤零零地耸峙在杂草丛中,让人联想着当年人们进收支拨的身影。

保康宁药行
此刻,统共这个词九华径,惟有咱们两人外来者走在小路上。旧村虽配置凌乱,破落生僻,额外行人,但也另有一番寂寞。沿小路上行,通常路旁出现一条胡衕,胡衕人家门口,大多拾掇得鸡犬不留,摆上几盆鲜花,显得颇为安静。走至屯子中间,小路旁,竟还有一个小卖部,其简略,远甚过内地深山里偏僻小村庄的小店。
王兄带着我,在一家门口停驻,与一位老伯用当地话聊天。王兄一边聊,一边用平凡话对我说,老伯在这里诞助长大,已有八十多岁,但他不记安妥年有一批内地文士在这里居住过。尽管如斯,我仍想与他合影,白叟欢娱搭理。偶然,他对咱们的寻访,也有一种好奇。
“村公所”铭牌、“养正家塾”额匾、门招牌……我逐个读过。我无法知谈,熟练的那些前辈,各自居住过的到底是哪一座屋子。然则,走在小路上,听潺潺流淌的小溪,看古树青苔,对一个寻访者说,足矣!
其实,访佛的走读,有时不在于一定要有具体的发现,任何与历史干系的嗅觉,都是走读的成绩,值得到味……
三、流一火者的“鱼米之乡”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九华径都算不上记号村庄,即便回到六十年前,只怕也算不上。但是,这里围聚绿树环绕,附进海滩,盘桓森林,荡舟入海,或游水,或打渔,不亦乐乎。难怪回忆在这里的良晌生存时,方成先生称之为“鱼米之乡”——
生存天然是贫苦的,但很茂盛。晚上几家人凑在一皆就吵杂了。其中最活跃的是黄永玉,他最年青,爱说爱笑,还有编见笑的天才。黄永玉和楼适夷、巴波三户住在一座小楼里,房间是楼板离隔的,碗碟之声相闻,过几天他就讲从近邻听来的趣闻。巴波也不恶浊,拿相通听来的见笑进行曲折。对文化人来说,见笑加饥饿会产生灵感,写出好著作来,况兼是养生之谈,这狡饰他们是不简短对外人谈的。咱们生存在一皆,鉴别喧嚣的城市。使命是各干各的,念书、学习都很专心,志同谈合,有着共同的联想和但愿。九华径虽在香港属下,却像此中鱼米之乡,诱惑着同声相应的人士通常打听。
——(方成《忆九华径》)
方成所忆天然可以,日常生存的削弱、纵容,带给宇宙痛快。不外,在我看来,对贻误九华径乃至其时旅居香港的许多内地文士而言,九华径带来的最大痛快,莫过于香港的隶属国特殊地位,使这些从内战硝烟和政事高压下贱一火而来的人们,有了开脱呼吸的可能。读不同人的回忆,可以得知,九华径其实是中共地下党为流一火而来的左翼文化界人士安排的一个避风港,具体崇敬此项使命的是楼适夷。
流一火者,急促来此,略作喘气,当大陆时期变迁场所活泼,国民党政权溃逃之后,他们再不竭北上,将九华径留在了死后。
臧克家在回忆录《诗与生存》中,曾回忆我方来九华径的进程。他说,一九四八年在国共内战强烈之际,他因写讪笑诗,裁剪左倾刊物而不得不逃离上海,来到香港后被安排在九华径,九华径是一个“不显眼的、有点诗意的寒村”。
巴波的妻子李琪树对逃一火来港进程的回忆,则愈加具体:
1948年下半年,我和我爱人巴波先后从成都到了香港。那是因为1947年景都的国民党反动派制造血流成河,不少一又友被逮捕了,巴波上了黑名单。咱们诚然躲到乡下鲁绍先家(郫县两路口,作者张天翼在他家养痾),但风声越来越紧,在成都已呆不住了。从报上表露,民盟总部已调度到香港(我和巴波都是盟员);从前来探望张天翼的友生齿中得知,许多爱国的文化人都不竭来到香港,咱们决定也去香港。
——(《楼适夷二三事》)
在这些曾生存在恐怖之中的文士来说,香港无疑是一个“鱼米之乡”。流一火至此的左翼文士们,既可以隐迹,更可以诓骗在香港正当出书的报刊,开脱地发表抨击国民党政权的作品。不再有追捕,不再有硝烟饱和,还可以开脱赞扬,其中的痛快,不言而谕。这就不难融会方成会将九华径称作“鱼米之乡”。
不外,所谓“鱼米之乡”并非全然如斯。九华径南来北往的人群中,萧乾、臧克家、胡风、黄永玉等,其内心未必水静无波。一九四八年前后,由左翼文化界在上海、香港等地发起的各式念念想批判、文化批判,风生云起。他们乃至关系密切的亲一又,被飞溅的浪花淋湿满身。比方并非舛错脚色的年青黄永玉,有益或意外,其时竟也在批判沈从文的进程中,成了一个陪绑对象。
对沈从文的批判早在一九四七年如故运行。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前后,曾有一些常识分子,如沈从文、萧乾、朱光潜、费孝通、冯至等,命令息兵,主张在国、共之间,走中立谈路,当场被训斥为“第三条谈路”。
一九四八年三月香港出书的《群众文艺丛刊》,刊发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一下子将沈从文、萧乾、朱光潜三人推到了反动的阵营。年青的黄永玉,一直与左翼文化圈战斗密切,不管何如莫得猜度,他也会受到批判。这一年的四月,上海出书的“同代人”文艺丛刊第一集《由于爱》,刊发公孙龙子《谈黄永玉的木刻倾向》一文,月旦黄永玉的景色办法倾向。值得在意的是,同期刊物另有对钱锺书的演义《围城》的横蛮月旦,另一集“同代人”丛刊中,臧克家的作品也受到月旦。
欧美性对黄永玉的月旦,与香港发起的对沈从文的批判简直同期进行,两者之间,有无告成商酌,虽有待史料证据。但是,在我看来,额外受到沈从文可爱的黄永玉,在刚刚精彩亮相并为《边城》配木刻插图之时,便招致来自左翼文艺界的横蛮抨击,恐不行当作是一次碰巧,或者一身事件。叔侄二人,第一次被系缚一皆,都成了实验批判的对象,想必是各自预见不足之事。不妨推测,那位在九华径喜欢讲见笑,享受“鱼米之乡”生存的黄永玉,削弱痛快的外在之下,内心想必多了精神的纠葛,多了历史的镇静。
恰是在九华径技能,因为楼适夷的一席话,黄永玉与沈从文有了一次特殊商酌。
我是从楼适夷先生那里听到的这件九花径旧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到北京使命不久,因裁剪《北京晚报》副刊,去看望楼适夷先生,请他为“居京琐记”栏目撰稿。自后他寄来一篇《一条拐棍》,从北伐讲和中友人执枪,说到“五七干校”我方用上拐棍,短短千字文,以手中拐棍听说半个世纪人生嗟叹,翰墨老辣,幽默而宽裕趣景仰,号称精好意思散文。
我很喜欢此文,请丁聪先生为之配上一幅插图——楼适夷手柱拐棍,腰板硬朗而站,笑眯眯的,慈蔼,谢绝。如今再看,那边有何足道哉九华径风浪人物的神情?
一九九○年,我为撰写《恩仇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再去采访楼适夷。他仍住在距我家不远的合作湖小区。此时的他,已卧床不起,虽不像几年前健谈,但谈及三十、四十年代文学界人与事,他依然意思意思盎然。
黄永玉致信转告楼适夷的话,对正处在慌乱之中的沈从文,是否果真起到了抚慰作用,不知所以。我所知谈的是,这一年的八月,沈从文渐次走出自裁的暗影,运行在历史博物馆使命,他致信仍留在香港的黄永玉,告诉他“这里的人只想劳动”,黄永玉将这封信发表在《大公报》副刊上。一两年后,沈从文再写信来,督促黄永玉一家回到北京,参加更生存。
算起来,在居住九华径的文士群体中,一九五三年岁首才抵达北京的黄永玉,大要是回到内地的临了一人。
文士走了,画家走了,小路上不再有人们熟练的那些身影。“鱼米之乡”,离他们越来越远,慢慢消散得荡然无存了。
四、记引李辉游九华径
新源兄有写日志民俗。自后,他发来当天日志,所纪录的畅游于今令人迷恋。谨将他所写的《记引李辉游九华径》日志一则转引如下,留存一份穷苦的行走牵记:
2011年6月20日
黄永玉的生平让李辉沉迷,查贵府半途,他说起黄曾居住九华径,我谈此村可能是九龙临了一个齐备屯子了;这时,李辉好奇心大起,详备问何如智力去;我谈该处在荔景与好意思孚之间,但离好意思孚较近;李拿出一份舆图,九华径根底未标其上,原本是旅局派发的免费舆图;后拿笔与纸问具体路程,看他如斯急切,且隔一天就要飞回北京;我说尽人之谊,上班前带路,并备上单反相机帮他拍几张好相迷恋。
吃晚饭时说起商榷贵府奇才「北李辉、南陈子善」,倒是陈子善深为人知,还未闻李辉。上网一查竟然名不虚传,仍铭刻他揭穿文怀沙面具,曾闹得沸沸扬扬,那本赢得楚辞巨擘名号的1953年版《屈原九歌今译》,仍静躺在我的书架上,可惜往后对李辉这个名字未留住深印像;我以为这也算是一个缘份,治服至少在香港,领有该版书及知谈作者其人,再识李辉的人如银河沙数。
次日下昼12时50分在好意思孚月台往荃湾线的车头处,我提早10分钟到了,李辉1时整到达,算是准时到达,由我带路往策画进发,他穿件T恤,斜背着背包,步行无邪、念念维显然、充满活力。照说跟我父母一般年齿,动做念维却年青20年;说他是大学者,熟练的人以为是,不熟练的难靠直观分别。
走路了15分钟到达村口,瞭望不易查觉是村,丛生的树木穿插在密密匝匝的斗室子之间,惟有走进去,才嗅觉到村子比联想中大许多。除了黄永玉,萧乾、端木蕻良等许多南来文士曾栖居在此。这处方位50年代之前委果叫作「狗爬径」,端木就写过《狗爬径牧歌》,并配黄永玉作的插图,但「狗爬」欠端淑, 50年代初倏得改了名,香港有许多以旅途定名的村子,另如「赤径」「显径」等,不知谈的还以为只是是一条路名。
村里有多座似乎是上世纪20-30年代已有的西法洋楼,顶部楼牌有「星星」、「花朵」等图案;另外还有一座列作香港作事的「养正家塾」,推断有逾百年历史,这些都可能是黄老对阿谁年代仍有回来的配置物。半途巧遇一位87岁的白叟家,他自言诞生在此村,在此住了一辈子,各处方位基本莫得篡改,跟上世纪40年代变化甚少,我请李辉跟他挽手拍了张合影,白叟跟当今的黄永玉一般年齿,言语时绘声绘色,虽不了解可能与名人做过邻居,方位简略却能乐天知命。
李辉赠我一册与黄有共同签名的列传,他指向书中一座屋子漫画,是黄40年代居住的九华径的创作以赠萧乾,竟酷似咫尺仍留传的部分不限定斗室子男同 影片,因此带人游不一定是损失,也能够增长看法的,就如同这一次。咱们当天走路在九华径村中的小路,穿过细窄的过谈,途经的多座院落中传出升沉不竭的狗吠声,仿佛重拾当年黄之视线。